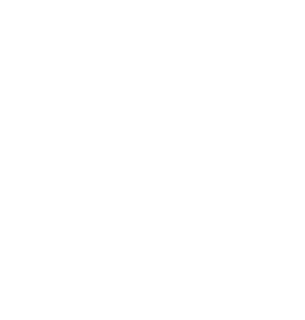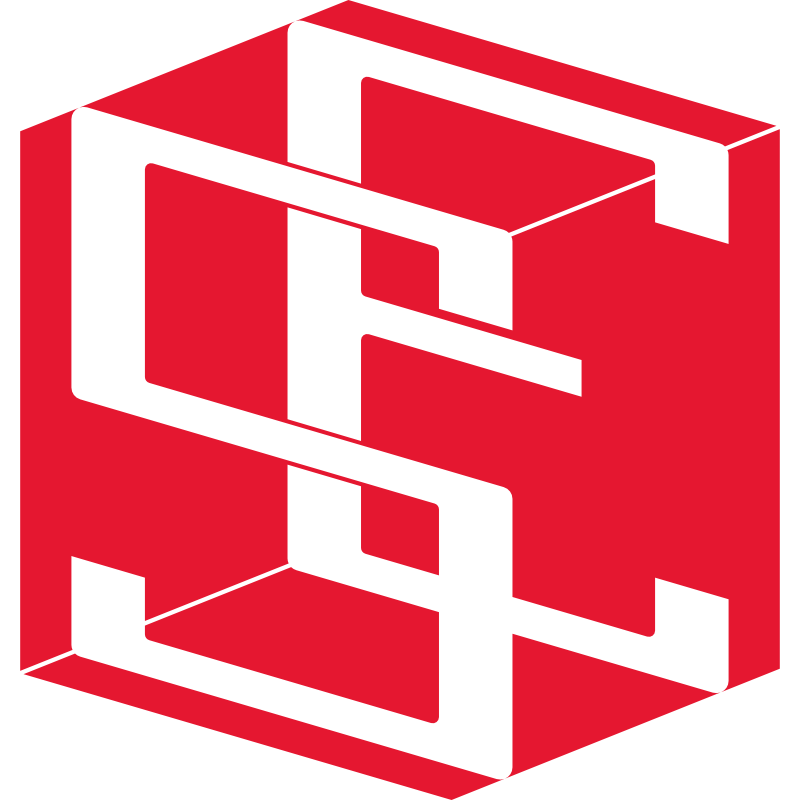 AI Search Paper
AI Search Paper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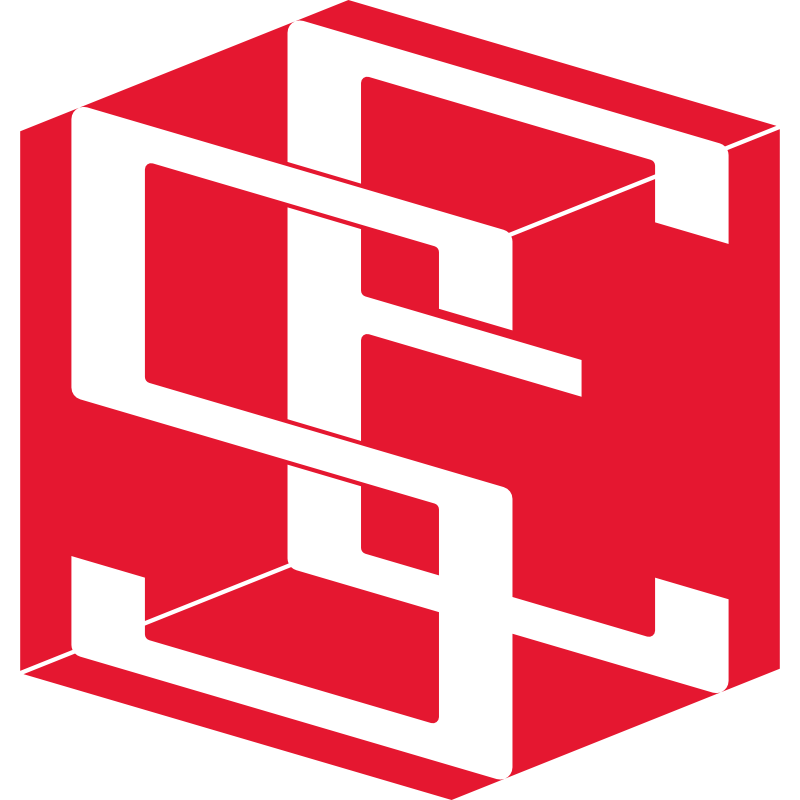 SciEngine
SciEngine
Abstract
References
{{author.surname}}
{{author.givenname}},
, et al..
({{ref.collab}}).
 SciEngine AI
SciEngine AI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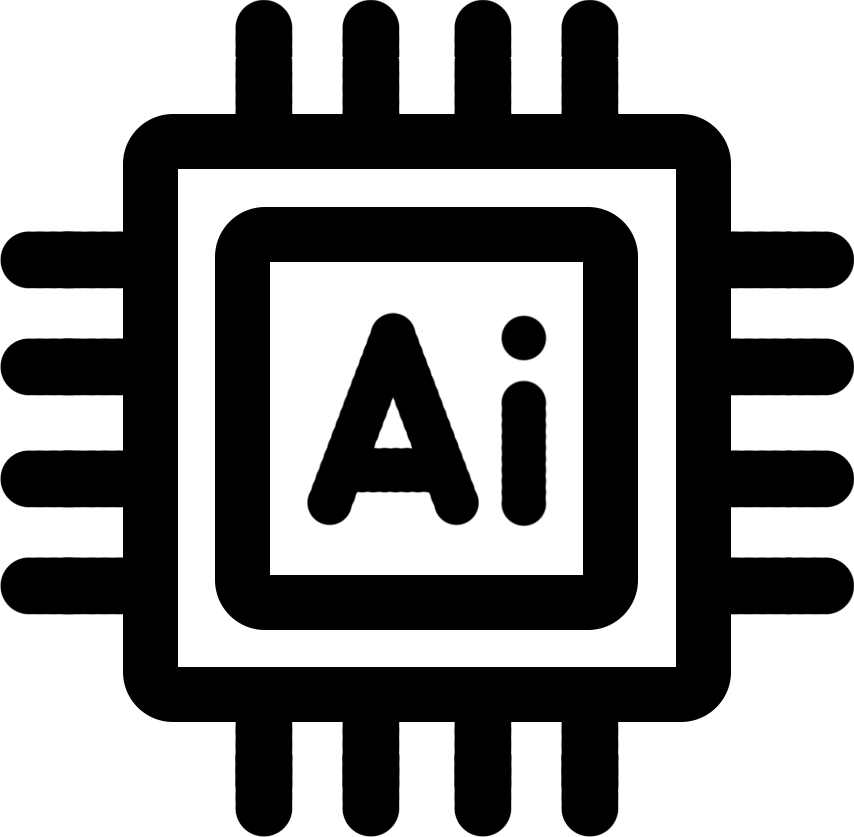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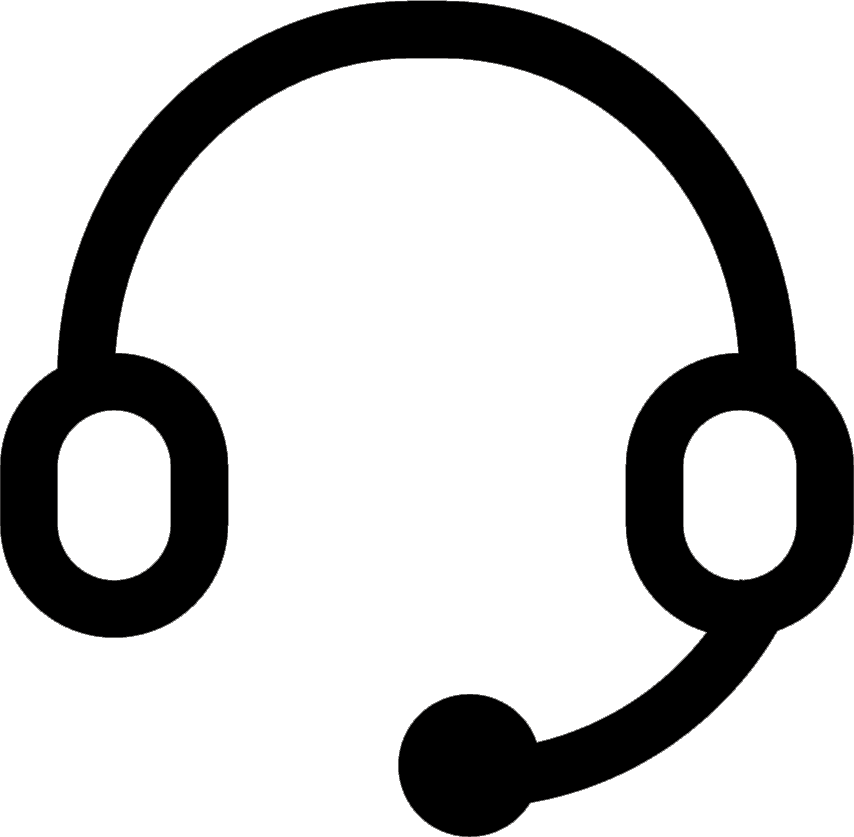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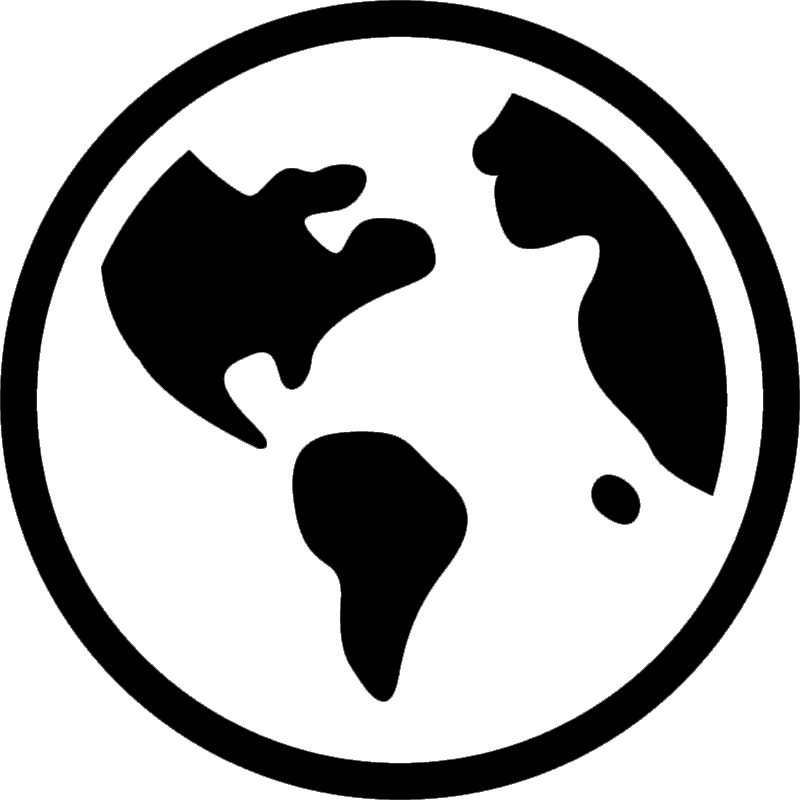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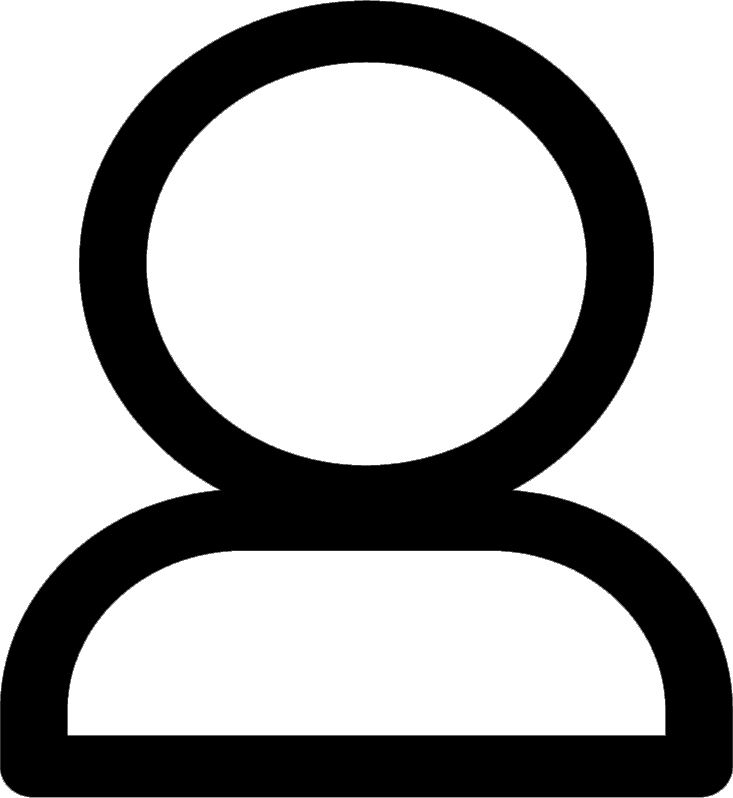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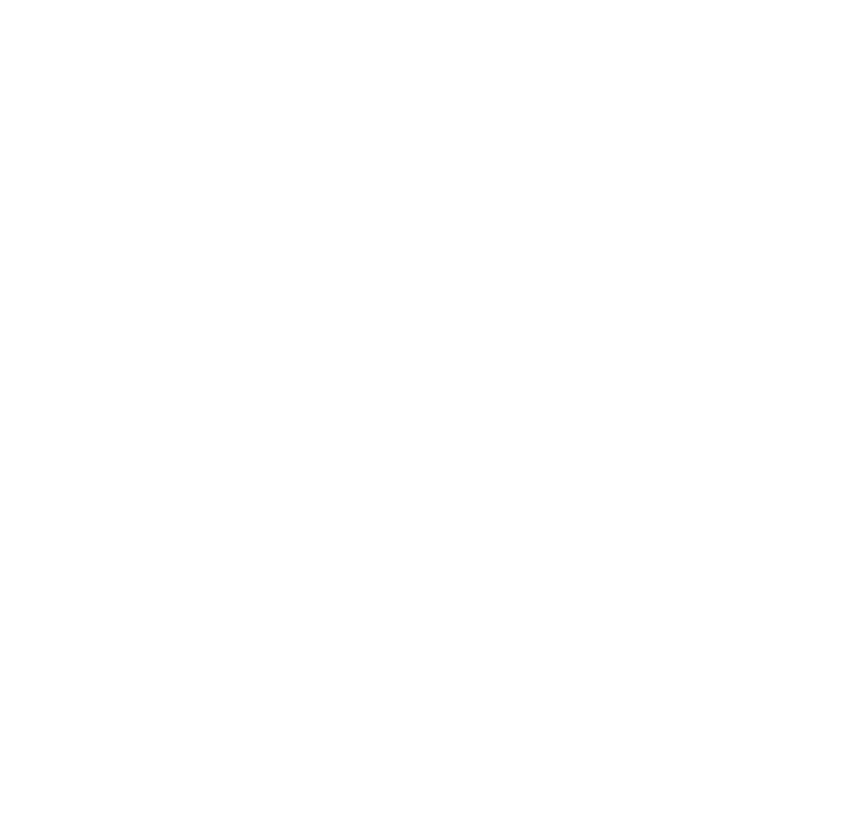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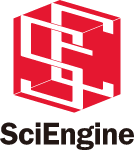









 Download PDF
Download PDF